厉以宁逝世——常识是简单的,但说出它的人并不简单
原创海边的西塞罗 海边的西塞罗
收录于合集#读书的小西塞罗23个
聊几本我看过的他的书,
其实老先生讲的大多数东西,无非常识。
各位好,开始正文前先给大家道个歉,昨天我在视频号那边预告了一次直播,最后却没搞成。放大家鸽子的原因其实是昨晚回完消息,就靠在沙发上睡着了,醒来时已经九点多了,让很多订阅的朋友白等了,实在不好意思。
近期出书、做视频等杂务杂糅在一起确实真的太忙了,而这种忙碌可能要持续到即将到来的3月:
下月初的时候,我会去长春听我很喜欢的国际问题专家徐弃郁的一个课程,月末可能去杭州参加一个笔会,中间或许会去北京或上海给那本新书做一个读者见面和签售……
总之这一个月可能都在路上,到处奔波,写稿只能用笔记本了,至于各地读者朋友的约见,我不知行程内是否有时间满足,只能说尽量。
虽然把日程安排的这么满,本就是因为想近期少说两句,多出去走走,享受祖国的大好春光,但我确实也很担心这样来回奔波会让自己没时间阅读、思考和写作,写不出用心的好文章来。
昨天跟一位读者朋友聊天,她在祝贺我新书出版的同时非常客气的建议我放缓写作速度,比如每周写个三篇稿子,多出一些精品。并委婉的说我近期有些 稿子没有之前那种给她“醍醐灌顶”的感觉了。
我听了这话,在感谢她提醒的同时,还挺委屈的——就说即将过去的这个二月,虽然挺短的,我一写一整天,用心构建叙事框架、并努力把故事讲好的文章也有不少,比如这几篇:
《三体》里这个著名实验,为啥伽利略根本不用做(重点推荐)
我自己觉得,写作依然很用心,怎么会给读者一种最近我精力不济的感觉呢?
但我内心里又害怕她说的可能是对的,忙的事儿一多,我最近留给自己静静思考的时间确实少了——看我文章时间长了的朋友,应该知道我的文字并非简单的史料集纳和新闻整合,而每篇文章必须搭一个叙事框架、有一个推论逻辑、最终得出一个观点,这导致每篇文章到底要花多长时间来写作,其实是不可统计的。
所以经常有同行朋友问我:小西,这篇文章你花了多长时间写的?我回答都是“很难说”。
一篇文字,我可能在十几天前就已经开始起心动念想写了,为此在当天和妹子约会时像个傻瓜一样经常掉线、走神,引她不满。而接下来这十几天里,这个念头会想孕妇肚子里的胎儿一样,不断在我脑中发育成型,打扰我的生活,而大脑中,我既往的阅读会给它不断添加血肉,最终当它彻底成型时,我也真的就像待产的孕妇一样,必须花上数小时的废寝忘食的将它写出来——不写难受。
这是一个甚至连我自己都无法控制的过程,有时我甚至怀疑过到底是我主动写了文章,还是这篇文章所蕴含的常识就天然存在在那里,只是它迫切的想要籍由我让它自己诞生出来——这个感觉可能真的挺像怀孕生产。
或者就像我很喜欢的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的那个段子:这人一生疯狂的肝稿、作曲,把五线谱、笔和小提琴放在枕头边上,以便一睁眼就能把脑中的旋律记下来,朋友劝他克制一点,注意身体,多过一点正常人的生活、细水长流。
可施特劳斯怎么说呢?“我有什么办法呢?那些旋律,他们自己要流淌出来。”
讲述小约翰施特劳斯的 故事片《翠堤春晓》
对写作者来说,这是一种矛盾,一旦你进入了这样一种写作状态,你就要抛弃生活、禁绝社交、一天二十四小时在梦游般的状态下想你那稿子。
可是人总要生活的,尤其当你闯出了一点点空间的时候,你要多去几个地方认识一些人、适当的出一两本书、找更多的朋友给你作为助力。这样,你未来的工作才能做的更好、争得更多的机会。
于是你又不得不时常从自己思维世界的象牙塔里走出来,去在这个世间走走,而这会打断你的写作进程……
想解决这个矛盾,需要很强的时间管理和自我调解能力,而出道刚刚两年,我现在还无法将它们平衡好。
嗯,我正活在坎上,大家见谅。等忙过这段,再多写些好文章。
以上都是谈心,下面说点正题。
刚刚看到新闻,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去世了。
我很想写几个字,因为我虽没上过他的课,但确实他的老读者了。
厉以宁教授虽然是个经济学家,但作为一个学历史的,我接触他的书特别早,原因是2006年的时候,商务印书馆出了一套他的《罗马—拜占庭经济史》。
我刚上大学那会儿正对罗马史最感兴趣,而经济又是一个观察历史必须的视角之一,所以就买来看了。
转到历史系呆了几年,我才知道,国内历史学界很多学者并不承认这本书是严肃的历史学著作。因为历史学讲究“论从史出”,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而厉以宁教授在该书中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用了经济学的写作方式,也就是先从观察中总结出一个自己的理论模型,再以这个理论模型选择性的使用史料,这在历史学者看来,有点“不地道”——类似你在足球场上抱起足球就来个三步上篮。
为这个事儿,我被很多同学嘲笑了很久:“看这段你不看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看什么厉以宁啊。”
但时隔多年,我依然不后悔(甚至可以说非常感谢)厉以宁的“非主流著作”能够成为我学习罗马史和经济史的双料启蒙读物。
因为需要“论从史出”的正经历史学著作,往往会把历史还原的过于纷繁复杂。而在这本书中,厉以宁教授以他作为经济学者的锐见,提出了一个非常简洁、有力、通俗、易懂的帝国兴衰模型:
罗马–拜占庭帝国的兴盛与衰亡,取决于它们对自身的中产阶层(中小商业者和自耕农)的态度。
当帝国重视并立法保障他们的权益时,帝国就会获得源源不断财税、兵源,即便是在强敌环伺夹缝中、即便敌人屡次兵临城下,它也依然能够崛起。
相反,当罗马–拜占庭帝国背叛和侵害了它德的中产阶层,用通货膨胀的铁钱去损害他们、用过度的税收去压榨他们,用土地兼并让自耕农破产,用皇帝敕令直接剥夺商人的贸易权时,帝国虽然能够通过这种竭泽而渔暂时性的讨好禁卫军、贵族或底层,但整个国家赖以维系的根基,已经在这种寅吃卯粮中腐败了。
所以厉以宁教授在书中说“整个罗马帝国从屋大维称奥古斯都算起、再到东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由盛而衰,由衰而亡,这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表明,兴盛时依靠的是自耕农和城市工商业者的支持……至于帝国衰亡的内在原因不仅是失去了自耕农和城市工商业者的支持……问题的关键正在这里:西罗马帝国也好,拜占庭帝国也好,自己把本来能够支持自己并且有力量支持自己的自耕农和城市工商业者毁掉了,自毁基础,焉有不亡之理?”
时隔多年,虽然看了很多其他相关著作,我依然觉得厉以宁教授提出的这个问题是最关键的——罗马(以及拜占庭)的衰亡,在于这个帝国先是在政治上抛弃、随后在经济上剿灭了它原本赖以力度的根本:中产阶层。
这是可能是“中产阶层决定国家命运”的常识在历史上第一次如此清晰的呈现出来,至于这个衰亡过程中其他的历史事件,凯撒遇刺也罢,屋大维中兴也好;查士丁尼再征服也罢、十字军东征反噬也好。不过是这个已经决定流向的历史长河中的一点偶然的波澜。
我们如果过分注视着那些波澜,津津乐道于坎尼会战、法萨罗会战、米尔维安桥之战、再征服运动、十字军东征、君士坦丁堡沦陷,而忘却了这条长河本身,忘却了是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而对“自由平民”的保障又决定了罗马的经济基础,那才真是得鱼忘筌——那些大事件,都不过是历史动机在充分发展后呈现出来的一个结果而已。
而很不幸,很多学而不精的历史研究者,其实总难免掉入这个窠臼之中,我觉得我们真的无资格以此批判“跨行”却看出了门道的厉以宁。
所以厉以宁教授谈经济史的书籍我一直是非常喜欢看的,后来我又去读了他的《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
我发现这位老教授写书有一个难得的优点:不同于很多学者写书时拉拉杂杂的谈半天,举了一堆的史料却让你不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什么,厉以宁在谈经济史时所最终想表达的观点往往都是一个可以用一句话总结出来的常识(这个特点特别像英国学者艾伦·麦克法兰)。
比如《资本主义的起源》一书想表达的观点也很清晰:是对私有产权保护、和私有产权的自我保护,最终催生了资本主义和近代人类经济上的飞跃。
而真正接触厉以宁教授那些更著名的、谈中国经济的书籍,反而是我毕业工作以后的事情,比如他有一本《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在业内据说评价很高,我读的观感是,除了某些篇目比较难啃之外,厉以宁对问题的那种“常识性洞见”是一以贯之的。
当然,在经济史、经济学著作之外,厉以宁最广为人知的其实还是他的那些发声:
比如他曾反对“减员增效”的提法,认为“减员增效从宏观来说,是根本错误的”,“政府不应该提倡“减员增效,”“政府的首要经济目标是增加就业机会”。
比如他曾大声疾呼教育的重要性,“教育的不平等引起就业不平等,就业不平等引起收入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引起生活不平等,导致下一代又不平等……教育经费应该占到国家财政支出的4%以上。”
比如他曾反对一些地方的城管过度驱赶小商小贩,“城市中,应该放宽对小摊贩的管制。在当前情况下,就业问题这么重要,你给人家开条路,给小摊贩留条路,不要让这些小摊贩整天躲来躲去的。”
这些关于时事话题的发言,都曾让厉以宁名噪一时,很多人为他敢于说出这些话而点赞,也让另一些人给他扣上“公知”的帽子。
但我始终觉得,今天,当厉以宁教授去世的时候,我们应该记住的其实不是这些。
作为一个学者,这个人的思想就像冰山一样,他在会议上、报章上的那些“厉言厉语”、那些“直言敢谏”只不过是这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
而在这冰山一角的下面,作为其基石的,是他对中国经济现象的深切反思和洞见。
而这种反思与洞见的基石,又是他对世界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史的研究与理解。
而贯穿这三层表达之内、一以贯之的是:厉以宁教授一直在坚持说一些常识。
是的,常识,经济学常识,今天很多经济学者动辄说一些“雷人发言”:什么鼓励老百姓掏空积蓄、贷款买房以刺激经济“爱国”啦,要求工人在疫情期间隔离到板房里坚持加班、保障生产啦……我觉得这些经济学“砖家”之所以可笑、挨喷,就在于他们经常聊着聊着就忘记一些基本常识:
比如经济的发展是为人服务的,不能给人创造幸福的经济数字毫无意义,
比如只有保障个体的产权利益、自由,社会才能繁荣,没有一个社会能通过限制达成繁荣与发展。
而厉以宁的很多书,读到最后,你都会发现他都没有忘掉这些最关键的常识——甚至很多书,从头写到尾,他只是反复在围着一两个常识打转。
这看似很简单,但其实非常难得。
我想起了观念史家以赛亚·柏林对学者的那个分类:狐狸与刺猬。
“狐狸机巧百出,不出刺猬一计守拙。”厉以宁教授一生研究了那么多经济学问题,从西方历史到中国现实,从罗马衰亡到小贩摆摊,看似是一个“狐狸型”的多知学者。
但被他这种“多知”所修饰的,是他的“一计守拙”——有一些他所坚守的信念与常识,是一以贯之的,他所变化的,只是论证和表述这些常识的方式。
我在想,我们的社会真的很需要这样的研究者、写作者,他们外表也许是“狐狸”,能够带着你神游环宇,从古罗马聊到当下中国,告诉你很多事情,但内心里,他们必须是刺猬,对那些无非常识的东西有一份坚守与执着,并在这些常识受到威胁的时候敢于亮出自己的厉刺。
是的,无非常识。
厉以宁教授去了,愿我们能有更多的学者、写作者、发声者能如他。
常识很简单,但愿意说出它的人并不简单。
他们值得我们——这些曾经受惠于常识、如今仍在常识、今后依然要指望常识才能过好日子的人——永远尊敬。
R.I.P
本文5000字,感谢读完,随笔一篇,愿您喜欢。
© 版权声明
THE 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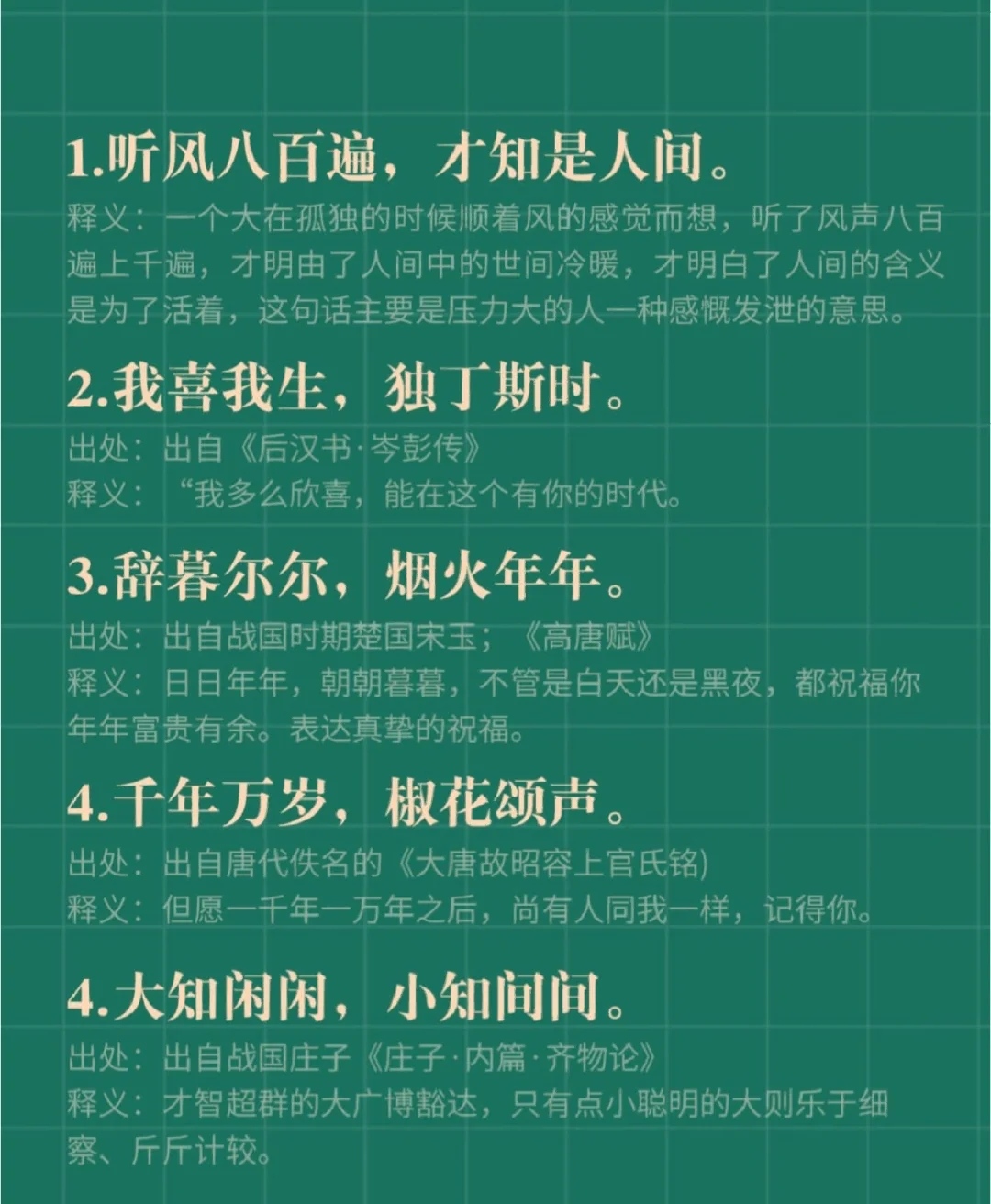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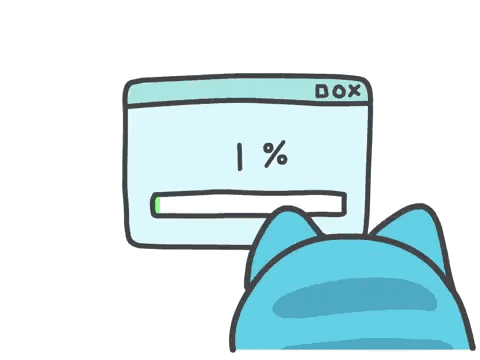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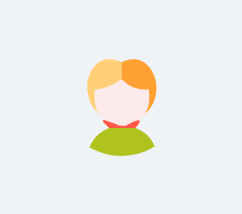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